2015年11月,蔣一談出版詩集《截句》,提出“截句”寫作理念,他說“截句,語言的出家人”。網絡上跨年的截句寫作從“卡丘微信讀詩課”開始,一些詩人一夜之間拿出了自己的“截句”。
我試圖寫出有我個人情感質地與語言節奏的“截句”,恰逢丙申猴年,我的本命年,也是我父親離開我一年多,我對他的懷念最為強烈的時候,我于是為“截句詩叢”寫下了這部《栗山》,獻給我父親的在天之靈。
進入《栗山》的寫作,我才發現遇到一個新的挑戰,如何在語言里留住更多的感受,如何在一行兩行三四行之內完成一首詩,要在“截句”里做一個“語言的出家人”,既符合我的本意,又是多么的艱難。對語言我不能有過多的非分之想,只有清潔之人才有清潔的語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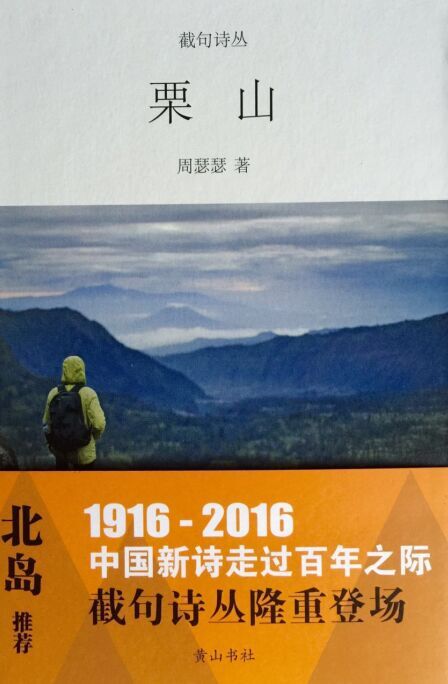
2016年,中國新詩一百年,在此時寫作與出版“截句”,也就有了新的意義。現在基本的共識是:“截句”是現代詩的新文體。我們已經不做新文體革命多年了,新文體的出現或許充滿了不確定性,讓人懷疑與害怕,懷疑其合法性,害怕其寫作的危險,當年的白話新詩不就如此嗎?我們在新詩“小富即安”的環境里太久了,不求變的“溫水煮青蛙”的保守心態是當下的常態,這是集體的退步。在中國新詩一百年的關口,“截句”寫作的出現,是一種新嘗試,是一種新文體的可能,它顛覆了舊有的語言表達習慣,是一個人精神清理與精神自溢的寫作,就像我小時候看到過的栗山上的樹自溢出汁液。它是向前看,而不是向后看的面向未來的具有現代性氣質的寫作,“截句”寫作需要你首先建立起一個牢固的結構,然后確立詩的精神,找到詩的呼吸,否則只會是單一的“句式”而不能成為一首完整的詩,“句式”也有生命力,但氣息不夠綿長回復。哪怕是一句,也應該有完整的結構,更應該有強大的精神體。有的人還在懷疑與猶豫,有的人已經動手了,只有動手才有希望,才能發現寫作一種新文體的不易。
新文體意味著寫作者首先要付出更大的勇氣,要打破既有的寫作習慣。除此,要發現新的自我,正如蔣一談所言:“要對自己下手狠一些”,我發現我在寫作這部《栗山》的過程中遇到了比想像更大的困難,我無法對自己下手那么狠,寫作這么多年,我雖然一直有變化的意識,但骨子里已經形成了很多固有的東西。
就像流水,在河床奔涌,在亂石中穿行而過,寫作《栗山》時我不斷調整詩的語感,慢慢繞開起先的些許不適應,一點點去接近理想中的“截句”。我在手機上寫了一部分,然后又移到電腦中寫,詩的感覺是充沛的,但要在“截句”新的形式、空間與結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,還是經過了一番愉快的折磨。
我愿意寫出個體的生命經驗,《栗山》中的個體是我詩歌最重要的審美,而生命經驗浸染了我全部的情感認識。《栗山》分為四輯:父親的靈魂、懷鄉、枯寂、愛是慈悲,我個體的情感線索貫穿始終,我不是那種能夠脫離自我的寫作者,我固守情感的底線。
我的故鄉在湘北,現在只有一座名為“栗山書院”的屋子留在栗山,門前有一口被栗山三面合圍的池塘,叫栗山塘。一到夏天,滿塘的野生雨水蓬蓬勃勃,蛙鳴徹夜如織,月夜下鯉魚泛仔,記得小時候我與哥哥就睡在塘基邊的竹床上。前年父逝后,悲傷的母親堅守了半年栗山,老媽媽過于思念父親,長此以往恐怕不行,最終在我們的勸說下還是住到姐姐家去了。父親離逝前兩個月,我回去拍攝父親的生活紀錄片,父親在我的鏡頭里用粗糙的毛筆為我寫下了“詩硬骨”,我把這三個字當作父親的遺訓帶到了北京。父親一生寫字無數,從不挑剔筆墨紙硯,信手拈來皆成好字,他走了,帶走了一手好字,想念他的異鄉深夜我就看那還留有他體溫的字,于是我也開始寫字。通過寫字,我想傳承父親容忍、淡然的生活態度。
大哥在微信里告訴我,“今日頭條”有人寫了一篇關于栗山“截句”的評論,我故鄉的一位家庭婦女讀到后哭了,我想她是熟悉我的父親、了解栗山的人。
在我的寫作體會里,我認為“截句”是一種生命的呼吸,世間萬物皆有呼吸,而我在“截句”里發現了詩歌語言、結構、精神的呼吸。你可以試著一呼一吸,呼吸是短暫的,不管你如何憋足勁用力呼吸,它是短暫的,但它又是綿長的,世間萬物要維持生命的秩序,必須要進行綿長的呼吸。就像古人相信生命是風吹來的,“截句”是生命的風,風斷了生命就止息了。父親臨終那一刻躺在我母親臂彎上,“他的頭一歪,就沒了呼吸……”母親告訴我。通過寫栗山“截句”,我在恢復父親的呼吸,父親沒了,只剩下了八十歲的母親,我覺得栗山的呼吸也微弱了。當我的肉身也被栗山埋下的那一天,我的呼吸將會完整的保留在這些詩里。
“截句”無疑是一種新的方法論,符合世界趨向簡單與尋求解決問題的規律,我甚至將它看做一種與精神相關的技術革命,如果把“截句”看做是一種從詩歌形式到精神確立的技術革命,也是恰當的。我的《栗山》就是在“截句”的形式里完成精神確立:父親的靈魂、懷鄉、枯寂、愛是慈悲這四條情感線索,是我當下最真實的精神狀態,這些“截句”沒有一句不與我最真實的精神狀態相關。
找到一種新文體,并把最真實的精神狀態給予它,它就有了生命。我們看過很多僵死的文本,失去活力的寫作困擾著我們,要從形式到精神走出來,必定要解放舊有的秩序,從精神上建立可以信任的新形式。
對《栗山》我充滿了感激,栗山是我祖先的山,我離開它快30年了,我現在把它寫出來,是對一座山的重新認識,是對我的精神體的靠近與確認。
2016年3月20日于京東樹下齋